工业题材长篇小说的天花板 ——评陈玉福长篇小说《劳模》

陈玉福四卷本长篇小说《劳模》
工业题材长篇小说的天花板
——评陈玉福长篇小说《劳模》
戴艺昕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陈玉福的长篇小说《劳模》以东北大地作为广阔的叙事空间,塑造出以章小凤、郝祖国、路鸣、郝立京等为代表的辽海工人形象。小说中纵贯百年的家族奋斗史展现出辽海工人群在历史浪潮中的坚守与蜕变。正如作品中表现的那样,劳模精神从个人的特性中提取,于多人的共性中展现,最终上升为一种精神符号。
在《劳模》中,劳模精神作为核心命题贯穿了整个作品。它不仅是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象征,更是时代与个人的精神交互。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符号,劳模象征着社会对工匠的崇敬、对奋斗精神的瞻仰与对时代责任的担当。随着时代的变迁,劳模的内涵被不断解读,并在陈玉福笔下呈现出分裂与重构的特征。

陈玉福四卷本长篇小说《劳模》诠释了工匠和劳模精神
正如费尔南多·萨瓦特尔在《伦理学与自由》中所言,个体在面对社会变革时,往往不得不重新定义其道德框架与行为准则。陈玉福将工匠置于广阔的社会工业背景下,摆脱以往作品中劳模的单一形象特征,将其塑造成复杂多元的历史形象,并通过多个形象的塑造,展现劳模精神在不同阶段的精神风貌。以往的劳模形象恪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在文学呈现中不可避免地存在“高、大、全”的问题,而陈玉福通过对人物内心挣扎痛苦的描写,再现了大时代背景下个体的真实心路历程,将劳模去“神性”而还“人性”,进一步揭示了劳模作为文化符号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
小说中的人物郝立京正是劳模形象新裂变与重构的最好代言人。郝立京是劳模的后代,也是第三代劳模的代表。他处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市场经济之下,在浪潮的裹挟中面对坚守集体与追逐个体价值实现的艰难抉择。正是这种内心的挣扎与痛苦映射着劳模精神的重构。在计划经济时代,郝立京是典型的集体主义践行者,经过痛苦挣扎后,他蜕变为市场经济探索者。陈玉福通过对劳模形象的重构,挑战了传统工业文学中对正面人物的书写,同时为劳模精神提供了崭新的诠释视角。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下,劳模不是单一扁平的意识形态符号,而是成为了具有多重身份和内心冲突的复杂个体,多面人格取代了单一人格。他们既象征着劳动精神的崇高,又浮沉于个人利益和社会责任的纠葛之中。市场化的进程往往意味着价值观的重构,传统社会道德的伦理基础往往被新的经济逻辑所取代。《劳模》的人物塑造角度不仅着笔于小处,即个体形象的嬗变,也着眼于传统价值观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碰撞。
郝祖国的人生经历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缩影,当权力身份与劳模精神产生冲突,道德困境成为决策的唯一议题。郝祖国从技术员一步步晋升为副省长,个人职业的发展与国家的政策走向交织在一起。在交织融合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效率逻辑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劳模精神在新时代的语境中得以被重新定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劳模》不仅是工业史诗,同时也对社会价值观、伦理层面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当男性劳模形象在社会价值观中发生解构和裂变时,静默的改变也在女性中产生。《劳模》以女性形象塑造见长。传统劳模形象往往以男性为主,突显力量与责任之重要性。陈玉福通过对女性角色的塑造,打破了传统的性别框架,使女性劳模绽放于工业小说的舞台上。章小凤以“女扮男装”的方式出场,既是对传统小说性别分工的一次深刻反思,同时也揭示了性别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不同于以往劳动型女性的“铁娘子”印象,陈玉福并没有将章小凤的性格停留在简单的概念上,而是移向了章小凤对工匠群体的影响。女性的参与打破了以男性为主导的工业空间,同时也给予了劳模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新解读。陈玉福试图通过章小凤的性别,找到女性角色在工业劳动中独特性的突破口,使章小凤以劳模的身份,成为时代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正是陈玉福的独到之处,写东北则不可不写工业发展,写工业发展则不可不写妇女形象的变迁。作为全国最早经历工业革命的东北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取代了人力劳动。由于在运用生产工具上的平等,女性前所未有地从性别框架中解放出来。在《劳模》中,女性劳模的崛起象征着时代对性别平等和劳动尊严的全新思考。章小凤作为辽海工人群当中的第一个劳模,甚至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她的形象塑造正是性别突破的最好表现形式。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有言:女性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历史的创造者。
可以说,《劳模》中的人物塑造既展现了传统劳模形象的复杂性,讨论了他们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解构与诠释,也通过女性劳模的性别突破,进一步扩宽了劳模精神的时代解读。陈玉福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展现着传统与时代的巅峰对决。
如果说恢弘的东北工业史构成了《劳模》的骨骼的话,小说的文化肌理则是由特定的东北地理符号和民俗、方言构成的。譬如骆子的快板词朗朗上口,既有方言特色又可见人物的内在智慧。章小凤作为一个典型的东北女性形象,她的奋斗与创造,总是与这片热土相连,她与东北的象征性互动带动小说从一幅工业图谱走向了一幅民族文化画卷。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人的存在总是与特定的地方密不可分。”从浅层表达看,《劳模》的创作特色是由地域景色、习俗来展现的,若向深处挖掘,东北在进行工业革命的同时也在进行文化血脉的塑造。

陈玉福四卷本长篇小说《劳模》封面
近年来东北文学迎来热潮,提起东北,工业、工厂等关键词是不可或缺的。在东北工业史当中,工人们的工作空间往往承载了一段线性的历史记忆和变迁。《劳模》对工厂的细致描写无疑增强了小说的现实主义意涵,也为东北工业基地的兴衰建构了一个文化集结点。在第二部《火红的时代》中,从章小凤整日泡在车间里,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到熔炉点火等细节刻画,时代的激情再一次在读者眼前点燃。作品以章小凤等人为切入点,进一步展现了东北人民对工业的深刻认同。《劳模》中的工业空间不仅具有推动历史进程的功能性作用,它同时也是东北工业基地草创期的见证者。当机器的轰鸣与硝烟弥散在上个世纪的余晖里,劳模则成了缅怀东北人民奋斗历史的一个小小缩影。
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陈玉福以独具地域特色的笔触,通过《劳模》中工匠阶层的跃升与利益纠葛中的拉扯和痛苦,生动地重现并再造了计划经济以及国企改革时期的东北式工业阵痛。文学与时代具有互文性,《劳模》四部曲恰恰与彼时的东北工业变革史衔接。这并非简单的还原,而是通过文学语言对文学时代使命的一次深切回应。
正如陈玉福所说:“劳模精神不是历史的遗物,而是时代的火种。”随着时代的变迁,劳模精神的内涵和外延正在不断发生改变,新的结构和生产模式正在解构着传统的劳动方式,劳模精神的传承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让劳模精神在文学中焕发生命力,将是新时代作家们共同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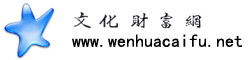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更多评论